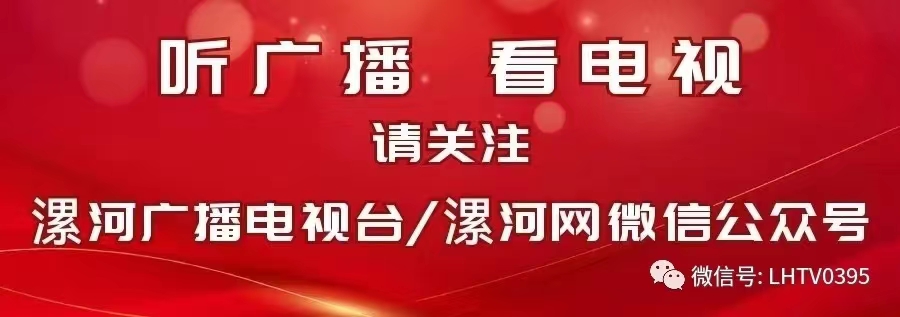仰望一所學校(3)
——記者采訪手記
◎盧子璋
(三)
話匣子彼此都打開了。他非常能夠健談���。我始終認為��,健談是一種思路或邏輯�����,前提是有底氣�����,而這底氣是需要知識和能力作支撐的���。
其實,他很早就是一名優(yōu)秀的教育工作者了����。在上個世紀九十年代�����,電腦還是一個稀罕物件的時候�����,他正是一家國字頭企業(yè)的一名職工;作為一個有前途的青年人�����,他被分配到電腦操作崗位��。他被培訓成熟練的老師后�,再去培訓單位的其他同事。
那一年��,他們單位要從南方搬遷到大西北��。這當兒��,他回了一趟舞陽老家��。縣城的幾個親戚����,還有同學,都把他當作了高科技人才�����,讓他抽空教一教電腦咧��。
那時間����,電腦打字還只有五筆,但那已經(jīng)是很先進的科技和很偉大的突破了���!那么復雜難記的字根����,像一道鴻溝��,讓許多人“望腦興嘆����!”���,不要說打開電腦進行打字操作了,就是開機也是無從下手?����?�!
面對大眾眼里復雜難記的字根與操作�����,朱喜洋是三下五除二便在屏幕上“盲打”幾段文字······
在政府部門工作的一位親戚���,建議他留下來,在縣城開辦一家電腦培訓學校��,給舞陽人注入一些時尚因子�。
當時電腦辦公的行情,還沒有露出端倪�����,各單位的材料還主要依靠手寫���,重要的材料文件�,也都依靠街上的打印社進行活字排版,街上打字復印的門店也還是鳳毛麟角�。
“你管管家鄉(xiāng)的文盲吧!”他的同學也把“電腦盲”升格為“腦盲”了�。
······
舞陽籍的青年小伙朱喜洋就這樣被輕易地說動了。他辭去了正式的工作���,在縣城開辦了第一家電腦培訓學校���。
為了走在時代前面,為了不當“腦盲”��,大家爭先恐后地來電腦培訓學校報名學習了���。他親自給大家授課�����。
后來���,他又在舞陽縣開了第二家、第三家���。
再后來���,他又把電腦培訓學校開辦到市區(qū)里去�。
談話順暢而愉快���。這個時間我們都才知道:多年前���,在市區(qū)大名鼎鼎的“綠葉”“星源”兩個電腦培訓學校原來都是他辦的呀!
他和他的電腦培訓學校�����,在漯河紅火了10多年���,他和他的學校也都獲得了不少榮譽。他本人是市���、省級的教育先進個人��。
也是在這期間�,他認識了在北京上海兩地搞傳統(tǒng)文化的一位著名教授����,深刻了解后�,很符合他在骨子里的對傳統(tǒng)文化的認同���。我們的教育就需要這個?����?!他當時心底里的一聲驚嘆���,至今還激蕩在他的胸間�����。
于是����,在“腦盲”掃盲已近尾聲的時候��,他關停了自己的電腦培訓學校�����,跟隨著這位教授去做傳統(tǒng)文化培訓的義工去了。不僅走南闖北地分文不取�����,而且還常常大把大把地進行過多次捐贈���。
他毫不避諱:他搞電腦培訓學校是賺了不少錢�,而且是盆滿缽滿的�����。
還有一句大實話也不必避諱——那就是����,他要是停下來休養(yǎng)生息,完全可以保證后半生及全家衣食無憂�����!
但是�,他喜歡上了傳統(tǒng)文化這項教育�����。他個人認為,我們當下急切需要的就是這個���,需要補上這一課�����。
讓他特別欣喜的是�,學生一旦被傳統(tǒng)文化的精髓浸潤�,就像是被灌輸了特別營養(yǎng)的樹苗一樣,驟然間就蓬勃挺拔地成長��,顯示出前所未有的樣子���,一下子就出類拔萃起來���。還有那些“差生”,很快改正了態(tài)度���,在人生的路上奔跑起來����。
他這年春節(jié)回舞陽老家過年的時候,有意識地做了一番調(diào)查�。傳統(tǒng)文化教育的不足,不僅是教育當下的共性問題�,他還發(fā)現(xiàn),突出的留守兒童的問題······
這些都撞擊著他的心���!
他決定自己開辦一所完小完中制的學校了��。
他的決心是那樣地大��。他甚至腦海里已經(jīng)跳躍出了學校的名字了——舞陽春雨國文學校��。
(未完����,待續(xù))
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
作者簡介:
盧子璋����,男,中共黨員�����,曾用蘆虓�、盧嘯林�����、司馬江虓等多個筆名。系中國作家協(xié)會會員��、中國詩歌學會會員�����、中國報告文學學會會員��、河南省報告文學學會副秘書長�。
出版圖書多種,多部被出版社二次印刷上市�����。其中《抵達遠古》代表河南人民出版社角逐第七屆魯迅文學獎�,次年選入全國中小學圖書館配套項目,后又被官方作為國際圖書交流項目與加拿大國進行圖書交流����,英文全譯本已在加拿大全新出版上市。
近百篇(首)作品入選多種文學選本���。其中���,《一座存放在春天里的城市》選入職高(中專)語文課本���。
另著有《開國將軍蘇進》《特別的情緣》《闖北京的漯河人》《大醫(yī)吳廣良》《輝煌的味道》《許慎與一座城》《軍中向日葵》等短中長篇報告文學作品,獲得國家省市多種文學獎項���。
現(xiàn)供職于漯河市廣播電視臺�����,新聞高級職稱���。被漯河市委市政府授予“漯河市第十批專業(yè)技術拔尖人才”、“漯河市文化領軍人才”等�����。
責編:瘦馬 編審:王輝 終審:盧子璋